马上注册,结交更多好友,享用更多功能,让你轻松玩转社区。
您需要 登录 才可以下载或查看,没有账号?立即注册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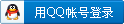
×
在清平镇,有一条春樱巷。
巷子的石板路总是泛着青苔,像是岁月轻轻敷上的一层薄纱。
第三间铺子,门楣上“陈记米铺”的招牌,已被风雨侵蚀得褪成灰白色,像一位暮年老人,无声诉说着往昔的故事。
陈寡妇站在柜台后,纤细的指尖轻轻抚过算盘珠子,那清脆的“噼啪”声,在这略显寂静的米铺里格外清晰。
突然,一阵强烈的恶心感泛上喉头,她脸色瞬间变得煞白,急忙扶住柜台,指节因用力而泛白。
她下意识地望向对面药铺幌子上那醒目的“悬壶济世”四个字,心里如乱麻般纠结,盘算着该如何迈出那艰难的一步。
“陈娘子,可是有了身孕?”药铺掌柜林鹤年不知何时来到米铺门口,他眯着眼,从那副陈旧的老花镜上方打量着陈寡妇。
林鹤年五十多岁,身形清瘦,总是穿着一件洗得有些发白的青色长袍,头发一丝不苟地束在头顶,透着一股医者的沉稳与精明。
陈寡妇闻言,身形猛地一僵,下意识地攥紧手中绣着并蒂莲的绢帕。
这绢帕是去年中秋,她那已然亡故的丈夫亲手所赠,也是他留下的最后遗物。
她微微点头,动作有些迟缓,像是不堪重负。
林鹤年的眼神却忽然变得意味深长,他轻咳一声,凑近了些,压低声音说道:“若有难处,不妨去城南找刘员外。他乐善好施,说不定能帮衬你一二。”
说罢,他意味深长地看了陈寡妇一眼,便转身回了药铺。
陈寡妇望着林鹤年离去的背影,心中满是狐疑。
刘员外,她自然是知晓的。
城南那座气派的别院,便是他的府邸。
平日里,刘员外常以善人自居,在镇上施粥、修桥,可不知为何,陈寡妇总觉得他身上透着一股难以言说的精明与算计。
但如今自己这般处境,又能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呢?思索再三,她还是决定去试一试。
暮色像一块厚重的幕布,缓缓落下,笼罩着整个清平镇。
陈寡妇来到了城南别院。
别院朱漆大门紧闭,门口的石狮子张牙舞爪,透着威严。
她深吸一口气,抬手叩响了门环。
不多时,门“吱呀”一声打开,一个家丁模样的人探出头来。
得知陈寡妇是来找刘员外后,便引着她进了院子。
院子里假山池沼、亭台楼阁错落有致,处处透着奢华。
陈寡妇无心欣赏这些,她的心像一只慌乱的小鹿,怦怦直跳。
在一间布置精美的厅堂里,刘员外正坐在太师椅上,手中捏着一枚翡翠扳指,那碧绿的色泽在烛光下格外夺目。
他身材发福,肚子微微隆起,脸上带着似有似无的笑意,一双眼睛却透着精明与世故。
见陈寡妇进来,他微微抬了抬手,示意她坐下。
“做我的妾室,孩子可以姓刘。”刘员外开门见山,声音低沉,带着不容置疑的口吻。
他的目光在陈寡妇身上肆意打量,像在审视一件待价而沽的货物。
陈寡妇盯着案头玉瓶里的并蒂莲,这与她帕子上的花样一模一样。
三个月前的那个雨夜,大雨倾盆,电闪雷鸣。
刘员外翻墙而入时,腰间所佩的玉佩也是这个纹样。
此刻,回忆如潮水般涌来,她的眼神中闪过一丝厌恶。
“我要做正妻。”陈寡妇深吸一口气,将手中的绢帕缓缓铺在檀木桌上,声音虽轻,却透着一股坚定。
恰在此时,雨打芭蕉的声音突然变得震耳欲聋,仿佛老天也在为她的这句话助威。
刘员外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,突然笑出声来,那笑声在空荡荡的厅堂里回荡,显得格外刺耳。
他用指节敲了敲案头的地契,冷笑道:“春樱巷的铺子连着宅子,作价三百两。你若应了,这地契便归你,以后也衣食无忧;若不应,哼……”
他没有再说下去,但威胁之意不言而喻。
陈寡妇紧咬下唇,心中恨意翻涌。
她知道,自己此刻是在与虎谋皮,但为了腹中的孩子,为了死去的丈夫,她只能强忍着愤怒与屈辱。
“此事,还需容我再想想。”她缓缓说道,声音尽量保持平稳。
“好,我给你三日时间,莫要敬酒不吃吃罚酒。”刘员外脸色一沉,眼中闪过一丝狠厉。
陈寡妇起身,福了福身,转身离开。
她走在回春樱巷的路上,雨水打湿了她的衣裳,寒意顺着肌肤直沁心底。
但她的眼神却异常坚定,心中暗暗发誓:“刘家,这笔账,我一定会讨回来。”
第二日清晨,阳光透过淡薄的云层,洒在春樱巷的石板路上。
米铺门口却围满了人,嘈杂声不绝于耳。
陈寡妇握着休书,脸上带着几分疲惫与欣慰,看着衙役将刘员外押走。
原来,昨夜从城南别院回来后,陈寡妇便将刘员外强占民女、伪造地契的证据,连夜送到了县衙。
县太爷清正廉洁,接到证据后,立刻派人调查,今日一早便将刘员外缉拿归案。
县太爷的签筒在晨光中泛着冷光,师爷站在一旁,展开状纸,声音像浸了冰水般冰冷:“刘怀仁,强占民女,伪造地契,罪证确凿。”
刘员外脸色煞白,额头上豆大的汗珠滚落,他怎么也没想到,自己精心布局,竟会被一个寡妇给算计了。
他恶狠狠地瞪了陈寡妇一眼,却也只能乖乖束手就擒。
但真正让巷口茶摊炸开锅的,是林掌柜在公堂上的证词。
“刘员外送来的安胎药里,掺了红花。”林鹤年站在证人席上,神色平静,声音却掷地有声。
陈寡妇闻言,下意识地抚着微微隆起的小腹,心中一阵后怕。
忽然,她想起三个月前那个雨夜,刘员外曾说:“你丈夫若泉下有知,该谢我替他照顾你。”
原来,从那时起,刘员外就已经起了杀心。
三日后,雨过天晴,阳光格外明媚。
陈寡妇抱着一个木匣,走进县衙后堂。
县太爷坐在案前,神色和蔼。
陈寡妇将木匣轻轻放在桌上,县太爷掀开匣盖,里面是半块羊脂玉佩,玉质温润,雕工精美。
“这是亡夫之物。”陈寡妇轻声道,声音带着一丝哽咽,“三个月前刘员外翻墙时,我拾到他掉落的半块。后来我发现,这半块玉佩与亡夫的那半竟能严丝合缝地拼在一起。我便猜测,这其中必有蹊跷。”
县太爷拿起玉佩,仔细端详,脸色渐渐变得凝重。
“陈娘子,多亏了你细心,才让这等恶人伏法。”他感慨道。
陈寡妇微微福身,眼中却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悲伤。
她知道,这场争斗,她虽胜了,却也失去了太多。
春樱巷的樱花开始飘落,粉色的花瓣像雪花般纷纷扬扬,洒落在米铺的后院。
陈寡妇在一棵樱花树下,埋下了一个陶罐。
里面装着刘员外伪造的地契,还有半张浸血的婚书——那是她与亡夫未及拜堂的证物。
她抚着已经平坦的小腹,对着樱花树轻声说:“放心吧,我会让刘家付出代价。”
城南别院里,刘员外的原配夫人正坐在佛堂里,将佛珠拨得哗啦响。
她五十岁上下,保养得宜,穿着一身华丽的绸缎衣裳,只是眼神中透着一股清冷与孤寂。
她忽然瞥见窗外闪过一道熟悉的身影,那枚羊脂玉佩在晨光中晃得刺眼。
“夫人,”丫鬟匆匆走进佛堂,禀报道,“陈娘子送来两担新米。”
刘夫人冷笑一声,将佛珠甩在案上:“告诉她,我要见她。”
陈寡妇跟着丫鬟走进佛堂时,刘夫人正将一把钥匙放进供果盘。
佛堂里香烟袅袅,气氛格外压抑。
“知道你丈夫是怎么死的吗?”刘夫人忽然开口,声音沙哑,像砂纸摩擦。
陈寡妇身形一震,眼中闪过一丝恐惧与愤怒:“你……”
“去年中秋他喝的桂花酿,是我让人掺了鹤顶红。”刘夫人直视着陈寡妇的眼睛,毫无避讳,“他心里只有你,即便娶了我,也从未忘记过你。既然得不到他的心,那就让他彻底属于我。”
陈寡妇指尖一颤,那把钥匙正压在供果下,形状与亡夫临终前塞给她的半把严丝合缝。
她突然明白,这一切都是一个局,一个由刘家精心策划的局。
佛堂外惊雷炸响,豆大的雨点砸落在地面上,溅起层层水花。
陈寡妇攥着钥匙冲出门时,正撞见刘员外带着家丁赶来。
原来,刘员外买通了狱卒,逃了出来。
“贱人!”刘员外抽出腰间佩刀,面目狰狞,“今日便是你的死期。”
陈寡妇却不慌不忙,她突然将钥匙抛向空中。
一道寒光闪过,钥匙被县太爷的飞镖钉在门楣上。
原来,陈寡妇早已料到刘员外会狗急跳墙,提前通知了县太爷。
“刘怀仁,你可知这钥匙是开什么的?”县太爷的声音从雨幕中传来,威严而冰冷,“你私铸铜钱的暗室,已经被查封了。”
刘员外闻言,脸色瞬间变得煞白,手中的佩刀“哐当”一声掉落在地。
他怎么也没想到,自己最后的底牌,也被陈寡妇给识破了。
陈寡妇望着刘员外那惊恐的眼神,忽然想起亡夫生前常说:“樱花开时,我就回来。”
原来,亡夫早已知道刘家的阴谋,一直在暗中收集证据,只可惜,他没能等到这一天。
雨停时,阳光穿透云层,洒在大地上。
陈寡妇站在米铺门口,看着县太爷带人抬走一箱箱铜钱。
这些铜钱,都是刘员外私铸的罪证。
林掌柜不知何时站在她身后,轻声说道:“陈娘子可知,刘夫人为何要害你?”
陈寡妇摇头,眼中满是疑惑。
林掌柜轻叹一声:“当年她与你丈夫青梅竹马,两小无猜。后来被刘家强娶,她心中一直怨恨。你丈夫娶了你后,她更是妒火中烧。”
陈寡妇心中一阵恍然,原来这背后还有这般纠葛。
她望着春樱巷的樱花,心中五味杂陈。
暮色四合时,陈寡妇在樱花树下挖出一个铁盒。
里面是亡夫的手札,记载着刘员外私铸铜钱的证据,还有他对陈寡妇的深情嘱托。
她忽然明白,三个月前那个雨夜,刘员外不是来偷情,也不是要当一个真正的奸夫。
而是,来销毁证据。
而自己的“身孕”,不过是亡夫布下的局,为的就是引刘员外上钩。
春樱巷的樱花谢了又开,开了又谢。
陈寡妇将米铺改成了学堂,取名“育英堂”。
她希望能在这里,培育出更多有学识、有品德的人。
一日,有个书生模样的年轻人来买米。他二十岁左右,面容清秀,气质儒雅,腰间的玉佩让陈寡妇瞳孔骤缩。
“请问可是姓林?”陈寡妇试探道。
年轻人微微一愣,随即点头:“家叔林鹤年让我来拜师。他说,陈先生德才兼备,定能教我许多学问。”
陈寡妇微微一笑,眼中满是欣慰。
她转身从柜台下取出半块玉佩,与年轻人的那半拼在一起,正好是个完整的并蒂莲图案。
“从今日起,你便是这育英堂的学生了。”陈寡妇轻声说道,声音中透着一股期许。
年轻人郑重地行了个礼:“学生林羽,多谢先生教诲。”
陈寡妇望着学堂里朗朗读书的孩子们,忽然想起亡夫的话:“知识才是最锋利的刀。”
她知道,自己的路还很长,但只要育英堂在,希望就在。
 |
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