马上注册,结交更多好友,享用更多功能,让你轻松玩转社区。
您需要 登录 才可以下载或查看,没有账号?立即注册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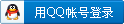
×
暮春的雨来得急,春桃在檐下收衣裳时,看见村口老柳树被风吹得乱发似的摇摆。她踮脚去够竹竿最末端的蓝布衫,忽然听见院门"吱呀"一声响。
"大川?"春桃抱着湿衣裳转身,瞧见个穿蓑衣的高挑身影正低头拴门。那背影听到呼唤明显僵了僵,蓑衣上的雨水在青石板上积成小洼。
春桃快步上前:"不是说去县里交粮三天才回?"伸手要接对方脱下的斗笠,却见那人猛地后退两步,斗笠边缘露出张陌生又熟悉的脸——分明是丈夫赵大川的眉眼,可轮廓线条更柔和些,倒像是二十岁的大川从记忆里走了出来。
"淋了雨...怕寒气过给你。"声音也是大川的,却带着老人才有的沙哑尾音。春桃正疑惑,对方已经侧身挤进堂屋,蓑衣都不脱就直奔东屋,木门关得震天响。
灶台上的粥还温着,春桃盛了碗放在东屋门外:"趁热吃。"里头传来打翻铜盆的动静,接着是声古怪的叹息。春桃贴在门缝上,听见"哗啦"的水声,还有...撕布料的声响?
二更雨歇时,东屋门开了条缝。春桃看见换了身旧衫的"大川"蹑手蹑脚出来,径直走向堂屋供桌。月光透过窗棂,照得他举着族谱的手白得发青。更怪的是,他翻到赵大川那页时竟抹了把眼泪,又去摸供桌后的暗格——那里藏着公公赵老蔫的烟袋,连大川都不知道位置。
"你不是大川。"春桃举着油灯突然现身,吓得对方摔了族谱。灯影里,年轻人左耳垂上的小痣与公公一模一样。春桃突然想起去年中元节,公公喝醉后说过他二十岁时在耳垂扎过痣"镇煞"。
年轻人颓然坐倒在太师椅上:"今早我去黑水潭钓鱼..."这开头春桃听了五年——每天清晨赵老蔫都这么说。可眼前人嘴唇开合间,露出的却是公公缺了半颗的门牙!
"爹?"春桃手一抖,灯油泼在对方手背上。年轻人不躲不闪,苦笑着摸出烟袋——赵老蔫的铜烟锅上磕碰的凹槽分毫不差。
原来清晨赵老蔫在潭边钓到条金鳞鲤鱼,那鱼眼里竟淌出泪来。他心软放生时,雷雨中传来个声音:"赐你青春貌美。"再睁眼,皱皮老手已变得骨节分明,水中倒影是个二十岁的自己。
"大川去哪了?"春桃攥着衣角发颤。赵老蔫摇头说不知,他变年轻后直接回了家。正说着,院外传来村长嘶哑的喊声:"老蔫哥!黑水潭漂上来个斗笠!"
春桃翻出大川今早穿的棕榈蓑衣——好端端挂在西屋。而赵老蔫的斗笠...此刻正戴在返老还童的公公头上!两人对视一眼,同时冲向水潭。
潭边火把通明,漂着的斗笠确是赵老蔫那顶,内衬还补着春桃上月缝的蓝布。更骇人的是芦苇丛里卡着只鞋——千层底纳着"平安"字样,是春桃给大川做的。
"水鬼找替身哟!"神婆王婆子突然尖叫,"你们看老蔫哥的影子!"众人低头,只见赵老蔫脚下的影子竟比常人淡三分,且轮廓模糊如水中倒影。
赵老蔫拽着春桃扭头就走。到家栓上门,他从怀里掏出片金鳞:"那鲤鱼给的。"鳞片在灯下泛着诡异的光,照得西墙上的合影像蒙了层纱——原本并排的三人,现在大川的身影正慢慢褪色。
三更时分,春桃被窸窣声惊醒。透过窗纸看见"年轻人"在院里挖坑,埋下个蓝布包袱。天亮后她偷偷刨开,里面是大川的旧衣裳,袖口沾着黑水潭特有的红泥。
"爹在遮掩什么?"春桃洗衣时发现木盆底沉着金鳞屑。突然有人拍她肩膀,回头看见王婆子凑近的脸:"你公公年轻时的相好就淹死在黑水潭...昨儿是那女人的忌日。"
春桃浑身发冷。她想起婚后第二年,有次公公醉酒念叨过"阿蘅"。跑去祠堂翻族谱,果然在赵老蔫二十岁那栏看到条朱笔批注:聘周氏蘅娘,未娶溺毙。
晌午赵老蔫拎着鱼篓回来,春桃故意说:"阿蘅姑娘托梦了。"对方手中活鱼"啪"地落地,鳃盖张合似在说话。当晚春桃假装睡下,果然见公公揣着香烛溜出门。
黑水潭边的老槐树下,赵老蔫摆开三样供品:糯米糕、绣线菊和半截红头绳——全是春桃昨日在箱底发现的,大川说是奶奶遗物。只见他焚香叩拜:"蘅娘,我儿是无辜的..."
潭水突然翻涌,金鲤鱼跃出水面:"赵老蔫,你儿子替你当了祭品。"声音竟像年轻女子,"当年你本该溺亡,是阿蘅用命换你。如今她转世需要替身,你儿子自己跳进了潭子!"
躲在树后的春桃冲出来:"大川还活着?"鲤鱼转向她:"明夜子时带赵老蔫的青春来换。"说完便沉入水中,涟漪组成个"川"字。
回家路上,赵老蔫突然说:"大川六岁那年,在潭边玩差点淹死。"月光照着他年轻的脸庞,"当时他说看见个漂亮姐姐推他下水...现在想来,那是阿蘅。"
次日黄昏,春桃发现公公在磨那把祖传的鱼叉,耳后新长出几根白发。子夜将至时,他将金鳞塞给春桃:"若我变回老头,立刻把鳞片扔进潭里。"
黑水潭边雾气弥漫。赵老蔫刚站定,水面就裂开个漩涡,浮上来个湿漉漉的人影——正是昏迷的大川!金鲤鱼在漩涡中心游弋:"想要儿子?拿你的青春来换!"
"且慢!"赵老蔫突然举起鱼叉,"按《水府律》第三百条,强取生魂者永世不得超生!"鲤鱼一抖:"你怎知...""我读了潭底石碑。"鱼叉尖挑着片写满咒文的龟甲。
原来赵老蔫白天潜水发现了阿蘅的墓碑,背面刻着镇压怨灵的咒文。鲤鱼暴怒地掀起巨浪,春桃趁机把金鳞扔向大川。鳞片触到他瞬间,赵老蔫的白发如雪纷落,皱纹重新爬上脸庞。
"爹!"苏醒的大川抱住衰老的父亲痛哭。鲤鱼长叹一声:"阿蘅,债还清了..."随着金鳞化作粉末,潭水恢复平静,只剩岸上三人相拥的影子被月光拉得很长。
回家后大川发了三天高烧,醒来却记不得任何事。只有春桃注意到,每当月圆夜,公公耳垂上的痣会隐隐作痛。而她自己开始梦见个穿红嫁衣的姑娘,在潭边种绣线菊。
秋收时县里来了个白胡子道士,说黑水潭怨气已消。赵老蔫送他出门时,道士突然低语:"其实你知道,那夜是你儿子偷了金鳞想变年轻..."老蔫猛抬头,看见大川正在院里磨镰刀,耳后有道浅浅的金痕。
"道长看错了。"赵老蔫笑着塞给对方一包烟丝,"父子哪有隔夜仇。"转身时,他摸出怀里那片偷偷留下的金鳞——已经褪成了普通的鱼鳞。
当晚家宴,大川给父亲斟酒的手有些抖。赵老蔫一饮而尽,哼起年轻时打渔的小调。春桃在灶间煮醒酒汤时,看见窗外掠过道红影,像极了梦中那个种花的姑娘。
 |
|